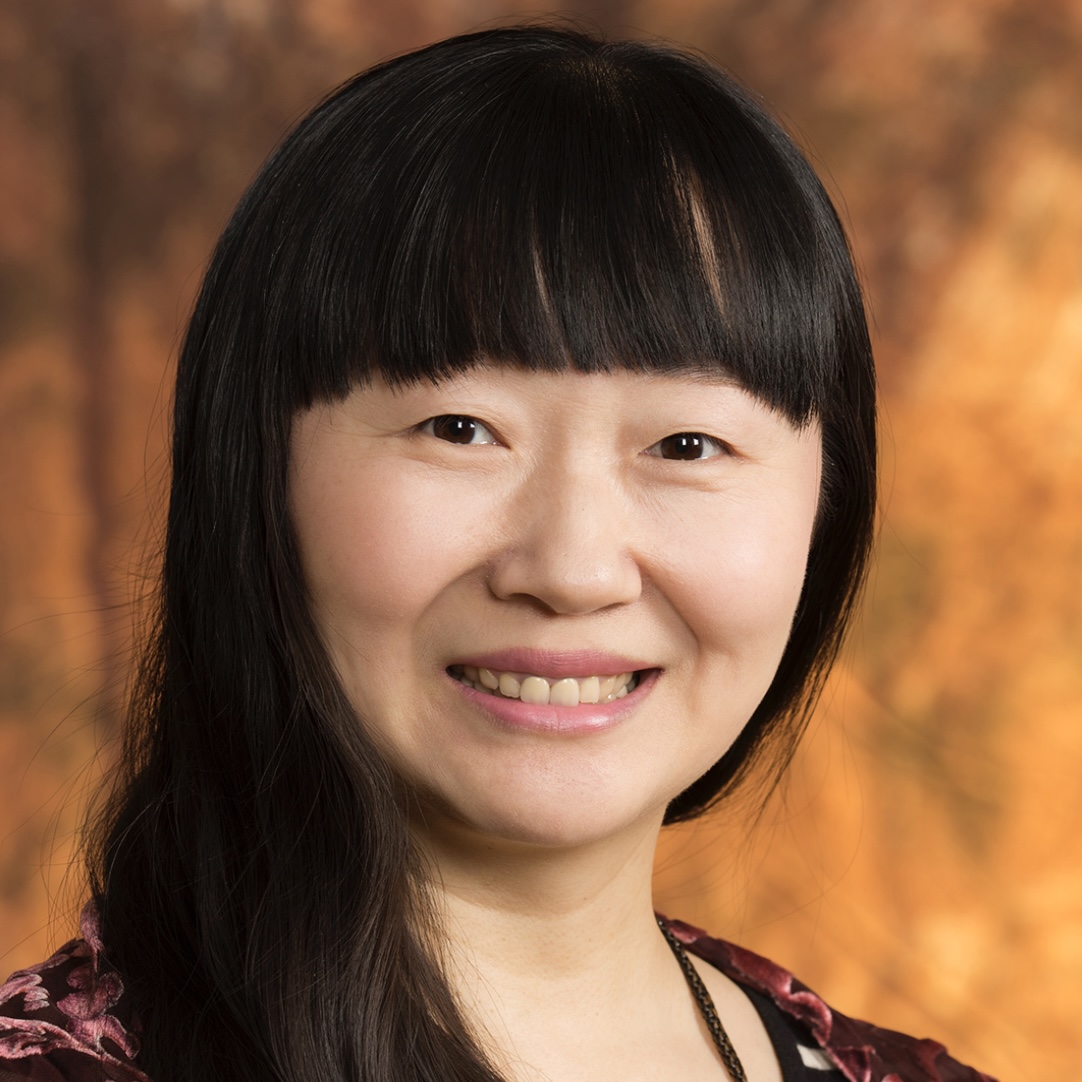王芳: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我国的应对之策
导读:
01
全球价值链正在呈现三大明显变化
《金融时报》记者:近几年,我们常常提到“全球价值链重构”,目前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哪些特征?
王芳:目前这一轮调整正在进行中,全球价值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上到宏观、中到行业、下到企业的各层级数据,也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首先是区域化发展势头明显超过全球化。一方面,区域化取代全球化成为最为活跃的国际合作表现形式。基于北美、欧洲、亚洲的三大区域内贸易网络更加紧密,美国、德国、中国在各自区域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节点地位进一步明确,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聚焦区域的贸易规则和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投资谈判的主要方式。不同区域协定的条款细节差异很大,比如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期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做贡献;又如美国推动的《美墨加协定》(USMCA)除了扩大产品和服务覆盖范围外,还规定了更加严格的北美原产地规则,设置了具有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和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从结果看,它们对于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有积极作用。
其次是全球价值链变得更长、节点更分散,北美和亚太的近岸化生产特征都很突出。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的进出口数据,还是企业层面的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的变化。中美贸易联系以及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和区域贸易格局中各自的角色和影响,无疑都是很好的分析视角。大量研究发现,中美直接贸易联系明显减弱,现在双方的最大贸易伙伴都已经另有其人;与此同时,墨西哥、越南、印尼等国家更多地嵌入中美之间,使得全球价值链拉长,而且更加多元化分散化。但是由于这些贸易伙伴强化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所以中美两国的间接贸易联系目前看反而增强了。北美近岸化表现,主要源于美国推动的产业回流和USMCA原产地规则,是主动而为的结果。对比之下,亚太近岸化则既有在美国打压下被动收缩的原因,将中国原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向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有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整个亚太地区贸易往来进行重塑的影响因素。
最后是不同产业的变动趋势高度分化。从智库和行业组织的研究报告来看,全球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更多强调战略自主,美欧日和中国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全球价值链调整集中反映了大国竞争的战略安全考虑。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以限制关键矿产资源开采或出口来保护民族产业的做法日渐盛行。相反,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转移,以中国为枢纽的亚洲工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更多低收入经济体被整合进入亚洲产业链,周边化生产、近岸生产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更紧密的贸易投资联系以及更紧密的产业链价值链联系,推升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使之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重心。
02
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观察应关注几个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谈谈导致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因素有哪些?应当如何看待全球价值链发生的这些新变化?
王芳:全球价值链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调整,其背后都有技术进步因素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也都深刻交织了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复杂背景,本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也不例外。
第一,大家都注意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显更加靠前,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力及其产生的破坏性远远超过成本收益等传统经济因素。2018年以来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各种形式的“逆全球化”政策操作,不断搅动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岛主义等社会政治情绪,一边推升了全球成本,一边制造着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全球断链风险的普遍焦虑。
第二,全球新冠疫情造成的“疤痕效应”仍在。疫情深刻改变了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对价值链各个节点的关系网络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建构安排,促使经济组织内部重新界定雇佣关系,推动全球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性变革。这可能使得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天然弱势”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陷入更大被动,对固链强链补链延链的需要极为强烈。
第三,地缘政治冲突推动能源市场重塑和制造业转型。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各国更加担忧全球价值链的安全问题,但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出现明显分化。能源出口国试图在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更多定价优势,并积极寻找更可靠、更长期的市场。能源进口国则一边加强能源合作化解危机,一边加快绿色能源的转型之路。制造业的这种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提高相关国家的个体安全,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和结构安全。
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观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既要看变化了什么,也要看引起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判这些推动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是否可持续,相关影响机制是否已经稳定下来。搞清楚这些,我们才能尽量排除价值链重构早期面临的干扰,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历史上每一次重大调整都不是匀速前进的,早期阶段出现试探、摇摆、反复甚至失败归零都很正常,而一旦方向确定、调整启动、布局完成以后,那么沿着惯性发展的加速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直到那些趋势背后的政治经济驱动机制的底层逻辑再次改变,才有可能扭转这个过程。国际产业总是要从政局不稳定、经济不安全的区域转移出来,但是观察到的产业变化特征,究竟是已经调整到位还是仍将继续调整,那些没变化的产业究竟是暂时还没开始调整,还是根本不可能发生调整等。搞清楚这些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也不要轻举妄动以至忙中出错。例如,美国已经在酝酿新的限制措施,欧美多国在高通胀压力下调整“双碳”目标,甚至宣布重启煤电项目等,这些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跟踪观察。
03
坚持走好“对外开放多边合作”的发展道路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面临什么挑战?要怎样应对?
王芳:中国是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工厂”和“贸易第一大国”。本轮全球价值链重构,本质在于有的大国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去中国化”。这些做法既对中国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也沉重打击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与安全。
中国面对的挑战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缺芯”“少核”仍是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力与竞争实力;二是“合作空间”受围堵挤压,中国与其他伙伴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因为新贸易规则谈判或排他性条款被迫削弱。
中国应对挑战需要紧紧抓住两个关键。一方面,短期看我国供应链安全主要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攻克“科创软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长远看必须坚持走好“对外开放,多边合作”的发展道路。要看到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动荡中可能遭遇“生存危机”。对此,中国在拓展国际合作、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除了提升自身整合供应链产业链的能力以外,也应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融资、跨境支付体系、国际政策协调等领域,重视弥补优质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口,以“更开放的中国”促进“更安全的世界”。
版面编辑|阎奕舟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